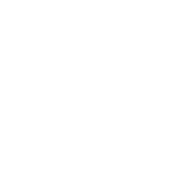跨性別演員艾略特·佩吉(Elliot Page)自傳回憶錄《佩吉男孩:他的破框與跨越》(Pageboy)已於10月26日出版,在這本深入而誠懇的自剖之書中,揭露了不少揪心的故事,比如出櫃後曾遭知名演員威脅的恐怖經驗,他與演員凱特·瑪拉(Kate Mara)、和凱特當時的男友麥克思·明格拉(Max Minghella)的三角關係,更自爆2007年拍攝電影《鴻孕當頭》(Juno)時,與同劇演員奧莉薇·瑟爾比(Olivia Thirlby)有過頻繁的性關係。以下我們一起來閱讀該章節的部分段落:
(延伸閱讀:《艾略特·佩吉曾被李奧納多湊對友人 李奧和媽媽也一起雙人約會!》)

《佩吉男孩:他的破框與跨越》。(圖/采實文化)
《佩吉男孩》書摘 第十章〈一場又一場同理心練習〉
我所飾演過的角色以各種方式影響著我。怎麼可能不受影響?那是一段探索另一名人類經驗的過程。一場永無止境的同理心練習,敞開心房,祈禱一切滲入吸納,等待那場情感的釋放。我會閉上雙眼,讓它襲來,一陣深不見底的絕望。我納悶她怎麼能撐那麼久。她怎能不乾脆放棄。我猜那就是折磨的意義,把你扯到了盡頭,又再拉你回去,一遍又一遍。
那時我住在銀湖(Silver Lake)一棟兩層樓房子的頂層,那一層被改建成獨立的公寓。公寓格局只有一房,美麗的市景透過大大的窗戶映入眼簾。房子隱身在露西爾街(Lucile)山腰上,離日落大道不遠,但遺世獨立,得爬一段相當陡峭的路。當時的我孤伶一人;我在洛杉磯時,身邊半個朋友也沒有。
我記得凱娜開著她的黑色轎車把我撈起來,帶我去參加一場美國國慶烤肉派對,就辦在巴斯特.基頓(Buster Keaton)住過的房子後院。我想她察覺到我被無以言說的處境給困住,所以想幫我。我們在她朋友Karen O對面坐下。Karen O 是我的偶像,〈現出原形〉(Show Your Bones)是我當時心目中最神的專輯。但食物讓我壓力很大,喝酒也是。我的眼珠轉來轉去,大腦停不下來,令我無法享受當下。
那陣子,我偶爾會和某個男人約會。我們會一起上餐廳吃飯,而我乾瞪著菜單發呆。我什麼都不想吃。我們曾去一間開在火車車廂裡,只供應義大利麵的餐廳。我們沒點餐就離開了,他開車把我送回家。
「我自己的問題,我早就處理好了。」他發動離去前說。
「我想我是同性戀,」有一次,我趁我們做愛時說。當下的我呈現一種封閉且疏離的狀態,甚至並非刻意在演。
「你才不是,」他回答,下身繼續抽動。
我幾乎不吃不睡,在片場恍恍惚惚。我強迫性地不停抽菸,期盼能呼出一切思緒。抑或如馮內果所說,「公共健康管理當局從未提及許多美國人菸抽得兇的主因,也就是:吸菸是一種相當堅定、相當高尚的自殺方式。」
拍攝工作變得越來越難受。我有時會睡在凱娜家,尤其是那些特別可怕的日子。待在她家讓我有被照顧的感覺。我們會坐在她的火爐邊一起喝龍舌蘭。我們大放音樂並跳舞、跳舞、跳舞,寬闊的未知冒險在眼前開展。我們因拍片而相識,拍一部她謀殺我的片子。現實世界中她卻是我唯一的浮木。
電影快殺青時,我暴瘦許多。等我回到偶爾還是會回去小住的哈利法克斯後,依然直線下降。我的體重掉到三十八公斤,手臂細到可以伸進外帶咖啡的隔熱套,一路穿過手肘、推到肩膀。我一天比一天消瘦。那年稍後的萬聖節,我打扮成咖啡隔熱套——小心燙口——用又黑又粗的馬克筆寫道。
無論多少關切的言語或眼神,無論旁人端出多少美味的點心試圖讓我吃點東西,我都不接受。我拒絕接受。傷害自己的身體傷害到那種程度一定是某種呼救,可是當援助果真到來,卻讓我既憤怒又怨恨。為什麼現在才來?這樣質問的確很偏頗。畢竟我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我在和怎樣的問題纏鬥。
殺青後第一次回家,媽媽的臉上寫滿了驚慌。她眼中的憂心讓我心碎一地,是一種我未曾見過的痛苦表情,而那罪魁禍首就是我。我跨過了一道檻,我的體重低到讓憔悴顯而易見。我對自己凹陷的雙頰感到害怕。
我渴望修復她、保護她,而這股慾望將我的飲食失調推上一個新方向。我現在想吃東西了,迫切地想吃。我不想讓她產生那種感受。
好不容易有了吃東西的動力,我卻做不到。當我準備咬一口三明治,只是一些簡單的,不是什麼太特別的食物時,我的喉嚨會緊縮,後頸開始冒汗,胸口湧上深深的恐懼。我的恐慌症大發作,無法嚥下嘴裡的食物。先前的我一直執迷於控制自己,如今竟全面失控。擠壓得太太太緊了。想當然爾,我的身體不願再聽命於我。
那東西不能進去。那東西不能進去。那東西不能進去。
日子兜著應該讓食物進入身體裡的時刻打轉。我的氣色像死人,身形骨瘦如柴,一切已無所遁形。我躲不掉壓力,躲不掉無所不在的擔憂。我也甩不開希維亞。我無時無刻都在想她。從來沒有一個角色像這樣卡在我的身體裡。地下室的片段。飢餓感。被迫吃下自己的嘔吐物。被忽視的慘叫聲。
「要不要試試看在花椰菜上淋起司醬?」一位諮商師好心建議。
我坐在她位於戴爾豪斯大學附近的辦公室裡,是間白色的房間,證書裱框展示,她有一頭波浪狀的淡色長捲髮,戴眼鏡,臉上架著一抹微笑。
「堅果是很好的零食,適合隨身攜帶。」
我們的話題環繞著早餐該幾點吃、該吃什麼,零食該幾點吃、該吃什麼,晚餐餐盤上該出現幾份的什麼。我不該去運動,不能做伏地挺身或任何之類的動作。我們只聊跟食物有關的話題。但問題全都與食物無關。
我避開我在哈利法克斯僅有的幾位朋友。我覺得很丟臉。「那個女演員」離開後又回來了,和其他人一樣。我就是一齣臭掉的老套戲碼。社交焦慮在此前已是我生活的常客,而當我的心理健康狀況惡化,孤立感便加重了,簡單傳個訊息給朋友都像是件不可能的任務,約出去見面更是天方夜譚。
過去,寂寞始終是我的主食,一種與生俱來的斷裂感,與周圍環境脫節,某種根本性的解離。我被引誘,蕩離自身,認為身邊的人巴不得我消失——認為他們比較想要我以一種假象存在。
我好一段時間無法工作。諮商師建議我休息一陣子,父母也這麼說。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,演戲都是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。我太脆弱,太不穩定,聲音一大就會嚇到我。肩膀被輕輕碰一下也會蜷縮。離開、獨處——生平第一次,全都成了不可能的念頭。過去的我一心只想自個待著,現在的我卻緊緊抓住任何能抓到的一切。抓住任何能感知到的一絲照料。
多數時候我遵照諮商師的規劃進食。吃飯時的壓力並未消失,意識到情況已經非同小可更是讓焦慮有增無減。我真希望其他人能停止關切,厭倦了那些「聊聊」和監視。當時,我有一個十分想要得到的角色,甚至還是個懷孕的青少女。我專注在《鴻孕當頭》上,避開最重要的問題。
零食這種概念幾乎不存在於我的生活中,很難想像睡前得吃點東西是什麼意思,但我還是會硬吞下去。我的體重開始上升。我喝用藍莓和酪梨和蛋白粉打成的果昔,喝完會脹氣。我漸漸學會吃零食,慢慢訓練我的身體重新學會去咀嚼、去吞嚥、去消化食物。學會保持冷靜,不必先喝醉再說。結果雖然仍不理想,但至少慢慢長回了一點肉。
我得飛去洛杉磯參加《鴻孕當頭》的最終甄選,其實就是類似試鏡。我是那種一旦覺得自己不適合某樣事物時總是率先承認的人,但這次,屬於那些非常難得的時刻之一,我才讀到第五頁,就無法想像自己不去做這件事,我就是知道。我是在我哈利法克斯家房間的地板上讀的劇本,蒂波洛‧寇蒂(Diablo Cody)寫的。她的機智塑造出一種獨特的語言——又自然又誠實。身為一名演員和一位觀眾,我一直渴望這種東西、這種角色。這個我做得到。
我還是過瘦,但好多了。媽媽陪我一起飛去洛杉磯。我從一個很小就獨立、十六歲就搬出去住的大人,變成一個需要母親陪同旅行的小孩。獨自出門在外感覺太危險,而我不能冒任何風險。好心的諮商師如此建議,但我不認為這是最好的判斷。隨著我對自己的酷兒認同更加堅定,她對我的否認也越來越強烈。
我媽當上老師之前曾在加拿大航空工作,不是空姐,而是機場地勤。她這輩子都很怕搭飛機。她會在起飛時閉上眼睛,緊緊抓住扶手。遇到亂流時,就會發現一旁的她心跳加速,全身好像在顫抖。我會安慰她沒事,一下就過去了。看見媽媽害怕讓我很心痛,感覺窺見了她的痛苦。她的一生經歷過很多痛苦。
飛機抵達飛行高度。我的焦慮開始蠢蠢欲動。在飛機上別無選擇,只能好好窩在座位上,哪裡也逃不了。我只好不停翻閱試鏡劇本。我在腦中默念台詞,一遍又一遍抄寫,幫助記憶。我媽總算冷靜下來,專心看起電影。
我們從哈利法克斯飛到多倫多,在轉往洛杉磯的航班上遇到了麥可‧塞拉和他爸。這次試鏡我得讀三十頁的劇本,多半是和麥可一起,是我參加過最長的試鏡。不過,由於我剛一口氣追完《發展受阻》(Arrested Development),心情很興奮,覺得麥可在劇裡的幽默感既獨特又著眼於現實,情感真摯不做作。我和媽媽的座位在機艙中間,麥可和他爸則坐在走道的另一邊。我們寒暄了幾句,他話不多,但態度友善。
起飛後,麥可立刻放下餐桌板,雙臂交叉趴頭就睡,而且一路睡到飛機準備降落。我在一旁看得欽佩不已,不敢置信。他怎麼可以如此一派輕鬆?我挪動身體,貼緊椅背,再往後仰一點,這個角度看得到媽媽的膝蓋焦慮地抖動。

(圖/@elliotpage IG)
雖然試鏡前就已經暗示角色會是我的,但是我接到電話時,心臟還是興奮地直跳。這也是非常難得的狀況之一——一個讓我充滿喜悅的角色。我被選中了,我夢寐以求的角色。
起初,劇組打算在試鏡後幾個月就開拍,但最後推遲了。推遲對我而言是好事,能有更多時間療養,沒有藉口可找。我在進食方面顯著改善,儘管還是會自我管束,但工作很有幫助。這部片拍起來很療癒,痛苦的片段不會跟著我回家,我也努力記得要滋補身體。情況仍不完美,但已大有改善。我找到了有意義的事可以專注,不像先前那樣,感覺一切都毫無意義,感覺憂鬱早已將我榨乾。
這份工作讓我感到舒適,有個穩定的立足點可以開始,而不是得努力從身體外面朝自己爬回去。拍戲時的髮型、造型和妝容往往是我的惡夢。諷刺的是,扮演一名懷孕的青少女,竟然是我頭幾次能在片場感受到些許自主權的時刻。我戴著假肚子,但沒有被過度女性化。對我來說,《鴻孕當頭》象徵了一種可能性,一處超越二元性別的所在。
待在溫哥華拍攝期間,我住在薩頓飯店(Sutton Place),也是部分業界人士口中的「爽一頓飯店」。那間飯店很雄偉,裝潢略有年代感,位於溫哥華市中心,設有演員經常下榻的長住套房。
我和媽媽共用一間有兩間臥室的套房。她是聖公會牧師的女兒,一九五四年出生於新布倫瑞克省聖約翰市,這讓我在拍攝期間交了女友的事情變得複雜。我的女友是第一個和我在雙方完整合意下發生性關係的女人。
第一眼見到奧莉薇‧瑟爾比(Olivia Thirlby)的時候,我吃了一驚。她舉手投足充滿自信與膽識,長長的棕色頭髮以慢動作飄逸。我們同年,但她看起來比我成熟、可靠、又沉穩。她的性觀念開放,與當時的我截然不同,但我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很明顯,深深吸引著我。我在奧莉薇面前總是害羞得令人尷尬。她經驗豐富,而我封閉自己。我幾乎很少對任何事敞開心胸,在她身邊卻讓我很自在,開始從殼裡探出頭來。我們很快就成為朋友,時常待在一起。

(圖/@sqirlby IG)
我們站在她的飯店房間裡。比莉‧哈樂黛(Billie Holiday)在背景唱著。她正準備要做午餐,突然直勾勾看著我,很乾脆地說:「我真的很喜歡你。」
「呃,我也真的很喜歡妳。」
我們就這樣熱吻起來。故事就此展開。
我對她的渴望是全方面的,她讓我以一種全新的、充滿希望的方式渴望。
這是頭幾次有人能讓我高潮,也是我第一次願意敞開自己。我們開始不停做愛:她的飯店房間、我們拍戲的拖車休息室,還有一次是在一間餐廳的狹小包廂。我們那時候到底在想什麼?我們還以為自己很小心。和奧莉薇之間的親密消除了我的恥辱感。在她的眼眸裡,我看不見一絲一毫的羞恥,而我渴盼如此——我不想再因為我是誰而感到痛苦。
我不知道媽媽那時候是否曾懷疑過什麼。她很可能只覺得奧莉薇和我很快就混熟了吧。這樣說也沒錯。但,我還是小心不讓她發現。奧莉薇應該只來過我的套房一次。

(圖/Getty Images)
我們偶爾會去麥可的房間玩,有一次,喬納‧希爾(Jonah Hill)也來了。那時他們剛拍完《男孩我最壞》(Superbad),但電影還沒上映。我們有大麻和琴酒。麥可拿出一架很酷的小電子琴,和喬納一起彈著玩。他沒在拍戲時會做點音樂,一直都是那副完美又煩人的酷樣子。我們都茫了,一起溜去溫哥華街上閒晃。我們晃去史丹利公園(Stanley Park),一處規模龐大、令人驚嘆的都市綠洲。那裡的樹木高聳參天,讓人心生崇敬。道格拉斯杉、美西紅側柏……有些甚至能竄到近七十六公尺高。所有這些時刻都是嶄新的冒險。
拍攝《鴻孕當頭》讓我重新振作起來,鼓舞了我,讓我變得堅強。
我們在冰壺溜冰場上互道再見,一場非常加拿大式的殺青派對。飛回家的路上,我的心好痛。我在多倫多轉機,登上了飛往哈利法克斯的航班。飛機穿越雲層、準備降落時,我正在聽爛桃子樂團(Moldy Peaches)。我盯著窗外,下方除了樹木、湖泊和河川以外,什麼都沒有。
那部低成本小片會成功嗎?飛機降落在柏油碎石跑道時,我思索著。突如其來的顛簸嚇了我一大跳。
(延伸閱讀:《艾略特·佩吉曾與凱特·瑪拉談三角戀:事後回想,當時我們幾乎都在做愛。》)
Source:采實文化、@elliotpage IG、@sqirlby I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