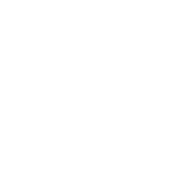跨性別演員艾略特·佩吉(Elliot Page)自傳回憶錄《佩吉男孩:他的破框與跨越》(Pageboy)已於10月26日出版,在這本深入而誠懇的自剖之書中,揭露了不少揪心的故事,比如出櫃後曾遭知名演員威脅的恐怖經驗,以及他與《驚奇4超人》(Fant4stic)演員凱特·瑪拉(Kate Mara)、和凱特當時的男友麥克思·明格拉(Max Minghella)的三角關係。以下我們一起來閱讀該章節的部分段落:
(延伸閱讀:《Elliot Page出櫃後遭知名演員威脅:「我要X你,讓你知道你不是同志!」》)

《佩吉男孩:他的破框與跨越》。(圖/采實文化)
《佩吉男孩》書摘 第二十四章〈出櫃之後,真正愛過〉
天下起了雨,但阻擋不了我們。我們繼續邊走邊聊,直到發現我們走到了西村,來到曼哈頓的另一側。她提議去珍飯店(Jane Hotel)裡如今已經關閉的吉塔內咖啡館(Cafe Gitane)喝杯咖啡,那是間位在珍街與西街交叉口的一家歷史悠久的飯店。咖啡館內的氛圍迷人而輕鬆,腳下是黑白相間的格子磁磚地板。店裡有種巴黎風情,揉合了別具一格的裝飾,好比說牆上掛了一隻鱷魚。我啜著美式咖啡,但我的胃只裝得下半杯。這時,我們兩個已經漸漸放空,疲憊感襲來,我們終於決定結束這場約會。我們起身道別,她吻了我,就在咖啡館裡。我的第一次。
這些時刻很美,但也很複雜,因為它們對我來說意義重大。
然而,心碎後的我,第一個真正愛上的人是凱特‧瑪拉(Kate Mara)。她當時有男友,是可愛又有才華的麥斯‧明格拉(Max Minghella)。我是在一場小型晚宴上認識他們的。初相識的那晚,我並未多想。凱特迷人又美艷,這點無庸置疑,但她身旁坐著男友。最主要的是,我忙著和麥斯深談,希望他能接下我當時正在製作並出演的一部片中的角色。不過後來,我與凱特又見面了。

(圖,合成照/@elliotpage IG、@katemara IG)
那時正值頒獎季,我的一位朋友克絲汀‧琪薇‧史密斯(Kiwi Smith)要在她洛斯費利茲的家為《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》(Blue Is the Warmest Colour)主角阿黛兒‧艾薩卓普洛斯(Adèle Exarchopoulos)辦一場派對。這種活動是頒獎季的日常,人們會為某個人或某部片舉辦派對,邀請奧斯卡美國影藝學院會員參加,盼望他們的支持能化作選票。這些就是讓我每天晚上得套上裙子、高跟鞋、化起妝出席的活動,也是年長男性會坐得太近、喝得太醉,脣上掛著汗珠對你說「你的夢想要成真了」的地方。
然而,這場為了阿黛兒‧艾薩卓普洛斯所舉辦的派對不同,是真摯且誠心的,就像琪薇本人一樣。這場派對是為了恭喜一位演員,慶祝一次難忘的表現,在她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的時刻接住她。身處於這個會把人榨乾的城市,這場派對是個小窩,不是陷阱。
那時我跟萊恩分手差不多才幾個月吧。分手後,我們偶爾還是會一起過夜。可想而知,一切又混亂又痛苦,但我不斷說服自己也說服她,這樣做完全是可以的。這沒什麼,我們可以當彼此的陪伴就好,我沒事,我希望妳和我都能過得好……一堆鬼扯。我過得一團糟,直到跟她斷了乾淨才變好。有好一陣子都沒聯絡。
我想她想得好難受。我想念她的氣味,那混合了汗水和防曬乳的味道;她的笑容;她手部的動作。我想念那雙手是如何隨著她的思緒、她的大腦、她的笑聲、她的神祕、她的眉毛、她的職業道德、她的好奇心、她的脣、她的嗓音、她的藝術、她的脖子——伸展的方式——她的書呆子氣和她的驚嘆而起舞。我想念每一件該死的小事,無法自拔,停不下來。我不惜一切代價想遺忘。
「重點是,我不想再繼續想你了。」瑪姬‧尼爾森在《藍》中寫道。
我也是,我希望能像《王牌冤家》(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)演的一樣,將她從我腦海中抹去。
我抵達琪薇家,穿過她高挑的玄關和壯觀的樓梯,經過她小巧的歌德風餐廳以及窄長明亮、設計精美的廚房,來到後院。熙來攘往的賓客都聚在這裡,還有專業的調酒師和外燴人員。我環顧四周,確認自己將獨自守著心碎度過今晚,派對上沒有一個朋友知道我之前和萊恩交往,就連琪薇也是。我祈禱萊恩不會現身,儘管她是我唯一想見的人。我沒把握今晚能順利撐過去。
凱特站在一群賓客中間,自然地和大家聊天,右手拿著一杯紅酒。她的側臉和那下顎的線條吸引了我。她熱情地和我打招呼,眼神煥發一種上次晚宴沒見過的神采,邀請我加入。她今天看起來比較放鬆,但不是酒精的緣故。她的酒隨著她說話而在杯中晃動,讓我思考起液體的搖擺是否能算是一種慣性。我提醒自己,她有男友了。所以當她開始和我調情,我以為只是開玩笑。更何況,不管她有沒有男朋友,我永遠都無法想像凱特‧瑪拉會看上我。
我們一來一往講了一些俏皮話,明顯是在互相調情。我不停轉頭向後看,看向不遠處的麥斯。
「哦,他不會介意的。」凱特注意到我的反應後說。
「那好,我等妳來,明天早上我會為妳做一份炒豆腐。」這下是半真心了的。
她笑了,我有能力逗她笑。我們站得很近,肩膀輕輕碰觸。
我吞了口口水。又看了麥斯一眼。
我們自然地結束談話,來來去去的客人吹起一波新的遷徙。我發現自己走到了院子的另一端,在一張木製長椅上抽菸,和初見面的人閒聊一些基本話題。剛才的調情讓我很興奮,但又覺得應該沒什麼,於是又繼續百無聊賴地閒聊。
我抽完最後幾口菸,菸已經燒到了品牌標誌,在這片刻的空檔,我注意到一名男子走了過來。他看起來很眼熟。
「嗨!」那人熱情地打招呼,沒開口問就一屁股坐在我旁邊。「你是萊恩的死黨對不對?我是麥特!」
我困惑地看著他。他投以一個大大的微笑,有點傻,有點煩。然後我想起來了,心裡隨之一沉,我就知道。
「哦!你們兩個是在……」我說,用手比了個在一起的手勢。
「對啊!她沒說嗎?」
一拳、揍上、肚子。耳鳴。心跳、當場、停止。
呼吸。
「哦,我不,呃……你們、多久……?」(比出同樣的手勢)
「一個月了!我愛上她,她也愛我。」他興奮地在長椅上一顛一顛的。「你呢,你有愛過嗎?」
我低頭看向地板,世界像K洞*一樣消失了。
哪個混蛋會這麼問?
他滔滔不絕繼續說著。聽起來像《史奴比》裡的大人。
我忍住不哭,勉強擠出微笑,但又不想笑太開,偶爾輕輕點個頭。
「她在哪?她會來嗎?」我看都沒看他,問道。
「不會,她開了一整天的會,太累了,現在在回我家的路上。」
*嗑藥到某個程度後,感覺自己瀕臨死亡、靈魂與軀體脫離的狀態。
一拳、揍上、肚子。耳鳴。心跳、當場、停止。
呼吸。
「抱歉,我去趟洗手間。很高興認識你,應該很快有機會再見面。」我丟下他,讓他自個兒沉浸在粉紅泡泡中——就像他的渲染帽T一樣活潑鮮豔。
恐慌膨脹起來,視線模糊,派對上沒有能求助的對象。我跑進主要樓層的客衛,坐上馬桶,立刻開始拉肚子。我身體裡的每個部位都能感覺到它的存在:悲傷,恥辱。就像掃到地毯下的灰塵,被拋在腦後,卻並未徹底處理掉。
我盯著鏡子裡的自己看(向來沒用)。然後離開了派對。我很清醒,開著車,雙手懸浮著,和其他部分分離,像個奇怪的小外星人在握著方向盤。我把它從體內排掉,現在我可以放下了,讓自己浮在半空。
到家後,我放起李歐納‧柯恩(Leonard Cohen)的專輯(無濟於事),就著煙囪抽菸(傷身害己)。為什麼我們受傷時會想要延長自己的痛苦?為了自我懲罰嗎?
我走去廚房倒水,好險還有喝水的力氣。我的手機響了——凱特發來了一封電子郵件。
哇,你的道別方式可真浪漫,謝囉。
我輕笑,笑容停在臉上的時間不合理地長。我點擊回覆。
說再見太難受了。
頭靠上枕頭,我想像起他回家找她的樣子。想像她等他回家的模樣。
重點是,我不想再繼續想你了。
最後我睡著了。
我和凱特繼續聊下去,我發現我們的調情不只是在開玩笑,對兩個人來說都是。我們說好一起去散步,也說到彼此生日附近時也許可以一起吃個飯?我們是雙魚座夥伴。
幾週後的情人節,我以同志身分出櫃。演說前我幾乎沒跟別人提起這件事。我希望那是屬於我的時刻,屬於我自己,不想再惹上八卦和臆測。演說造成了很大的迴響,套句年輕人的說法,就是「爆紅」了。
凱特發來電子郵件。
什麼?你是同志?!
我回。
對。接下來就看妳的囉。
出櫃的隔天,我飛去蒙特婁為《X 戰警:未來昔日》(X-Men: Days of Future Past)簡單補拍一些鏡頭。
「你好像變了一個人。」一位製作人對我說。
沒錯,我卸下了無謂的負擔。我的身體感覺更加有力,頭抬得高高的;我變得更親切,沒那麼心煩意亂,眉頭也不再緊皺。我正在路上。
幾天後,我在飛回洛杉磯的班機上坐定,一位牧師和他的助理牧師經過我身邊,他們的位置在我後面。助理認出我是誰,他的態度親切而友善。出乎我意料之外。
我一邊讀著劇本,一邊斷斷續續打起盹。飛行了幾小時候,我感覺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左肩。是那位牧師和他的助理。他們遞給我一張對折的活頁紙。是張紙條。我愉快地笑了笑,轉回位置上看。
我打開紙條,期待讀到一位支持 LGBTQ+的進步派宗教領袖捎來的溫馨鼓勵。
沒想到事與願違。
他在紙條開頭寫道,他的助理認識我,但他不認識。
我擅自上網搜尋了你。(不妙)
他接著說我的身分是假的。只不過是一種想法。
你的靈魂在掙扎。你需要投奔天父的懷抱。(噁)
最後,我真的沒在開玩笑。
署名,你的天父。
距離降落還有幾小時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。該說點什麼嗎?要回信嗎?我暗忖,但又有什麼意義呢?確實。三言兩語不可能讓他改觀,而分給他任何一丁點時間都會讓毒素沉積。於是,我把紙條折好,塞進口袋,繼續忙我的事。飛機降落,歡迎回家。
一個多月後,凱特邀請我去她和麥斯位於銀湖區山頂的家裡烤肉。麥斯已答應出演《走進希望無限的森林》(Into the Forest),我很期待見到他一起慶祝一番,他將飾演我的曖昧對象。他們家很有家的味道。舒適溫馨、裝潢漂亮、很有人味。客廳的沙發是會讓人忍不住窩進去的那種,而且是白色的,我實在不解他們到底是如何讓它保持潔淨如新。我總是弄髒所有東西。廚房很小,似乎從一九三〇年代房子建好後就一路維持原貌沿用至今。水槽,灶台背牆,一切都很完美。從廚房的門出去,會進入一個寬敞陡峭的後院。客廳外是露臺,
下方有一座火盆,還有一塊專門給她兩隻波士頓㹴玩的地方。
我們擁抱彼此,那是個長長的擁抱。接著進入介紹時間,派對的賓客我幾乎誰也不認識。凱特和麥斯烤起了素漢堡和一般漢堡。我和凱特挨著彼此,坐在連接房子和火盆的台階上。
我們坐得很近,而且開始打情罵俏。麥斯就站在附近,但他完全沒多看一眼。我們之間的感覺來得直接,彷彿具有磁性,而且最好是放在心裡、讓一切盡在不言中的那種。幾天後,我們終於有機會單獨出門見面。我開車去她家,再一起出門散步。我們爬上她的運動休旅車,她的兩隻狗也坐上後座,一起出發前往銀湖水庫。感覺依舊不變。藏不住的微笑。刻意避開的目光。
我們開進她的車庫,她熄了火。我們心有靈犀地在寂靜中多坐了幾拍。
「我們應該盡快找一天一起吃晚餐。」凱特說。
我沉默半晌才開口。
「約吃飯好像不太好。」我回答。但這其實是我用來表達我們很該一起吃飯的方式。
車內再次陷入寂靜,氣氛緊繃。
「我可以先問麥斯,和他說一下,我相信他不會介意。」
我微微頷首,努力藏起微笑。我沒料到她會這麼說,但這正是我想聽的。這股感覺千真萬確,宛若電流流經般溫暖。我渴望待在她身邊。
「好吧。如果麥斯沒意見,那當然好啊。」我說。
他真心不介意,完全沒意見,還很支持凱特多多和我相處、變熟。
於是,我們約好隔週碰面,一起去一間西好萊塢的餐廳吃飯。
凱特先來我家碰頭。我一打開門,便見到她臉上掛著那副表情、那種微笑,以及又甜又堅定的眼神。我們的脣首次相觸,傳遞一陣顫抖,讓我的膝蓋差點一軟。我們朝沙發晃去,舌頭相互交纏著。
凱特拉開距離。
「還不行,先去吃飯吧。」她說。
我們沿著月桂谷上坡,經過穆荷蘭大道,往西好萊塢方向前進。Uber司機在我當初第一次迎上萊恩海報凝視的轉角右轉。凱特方才剛到的時候,我的注意力被分散了,此刻有街燈灑入,我終於能好好看清她的樣子。黃色和紅色在她周圍鑲出一圈耀眼的光暈。她的暗金色短髮在向後飛逝的光線下微微閃爍,黑色緊身褲緊緊包裹住她的大腿,我盡量避開不去看。她的黑色外套底下穿著一件灰色T恤和一件敞開的襯衫。
如果人們看見我們,會覺得這不過是場普通的約會。我們碰觸對方的方式、凝視對方的方式,還有我們整晚是如何大笑不止。沙拉、薯條、龍舌蘭、葡萄酒。她的風采是如此鮮明,姿態是如此爽朗,單單眨個媚眼就能讓整個空間消失不見。
那天晚上我們準備搭Uber回我家時,被狗仔拍到了。我彷彿置身於另個時空,所有「被抓到」的焦慮都灰飛湮滅。我們到家後立刻進了我的臥室。凱特仰躺著褪去衣服,我則站在床邊脫下我的。我上床,爬到她身上。我們的嘴交融,身體第一次相遇。我吻著她的脖子,手放在她的大腿內側,手指緩緩向上游移。
第一次約會相當成功。於是接二連三。
我們會和共同朋友一起玩,或是一起參加派對,人們都以為我們在交往。
我們之間沒有羞恥或躲躲藏藏,只有毫不掩飾的吸引力。我很快就知道我們之間不僅是肉體關係,也不僅是化學反應的碰撞,而是打自內心的在乎。現在也依然如此。我們彼此相愛。
約會了幾次後,我便知道自己陷進去了。我無法停止想她。回憶會一閃而過,讓你在開車前往會議的路上沒頭沒尾笑出來。訊息打打停停。為一個措辭糾結七十二小時。想起那個人。
第一次約會不久後的某個早晨,一場地震讓我從床上驚醒,心臟都快要跳出來了。大腦叫我站在門框下,於是我乖乖照做。雖然後來發現那是錯誤示範,然而,那個當下我還是站在那裡,等到搖晃漸漸平息才大大鬆一口氣。現在我知道該怎麼應變了;為了讓大家保持資訊同步,請看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是這麼說的:
如果可以,請躲到堅固的桌子或書桌底下。盡量遠離外牆、窗戶、壁爐和懸掛物品。如果你無法離開床鋪或椅子,請用毯子和枕頭保護自己,不被掉落物品擊傷。
當一切都平靜下來,脈搏也恢復平穩後,我拿起了手機。我的第一直覺要我傳訊息給凱特,關心她是否安好。這個念頭來得措手不及,但感覺有點太過頭了,一切都是全新的感受,我提醒自己對方還有男友,也提醒自己有責任別當個混蛋。我準備煮點咖啡來喝,於是放下手機走向廚房。叮!我回頭一看,是凱特,她傳訊息確認我一切沒事。我盯著訊息,再次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輕笑。完蛋了。
曾經有個時刻令我難以忘懷,忘不了察覺的瞬間,也忘不掉消逝的剎那。
那是場由史派克‧瓊斯(Spike Jonze)主辦的雙壽星生日派對,主角是史派克的友人和友人的女兒,合併慶祝各自的五十歲生日與十六歲生日。派對辦在一間老學校,主樓層的禮堂是大人專屬的空間。現場請來樂隊演奏,人們伴著音樂喝酒起舞。學校那棕色米色相間的色調為夜晚增添了雋永的光澤。
我們手勾著手上去屋頂,那裡是十六歲生日區。高高的鐵絲網圍籬圈住整個屋頂籃球場,球場上的青少年閒來晃去。派對請來的 DJ 正在播放勁歌金曲,但沒有一個孩子在跳舞。我猜他們在討論怎樣才能搞點酒來喝,或醞釀著任何其他洛杉磯孩子都會做的事。
這裡的 DJ 比樓下的樂隊更對我們的胃口。碧昂絲(Beyoncé)、蜜西艾莉特(Missy Elliott)……我們二話不說便投入在音樂裡,迷失在搖擺中,凱特是唯一聚了焦的事物。感覺全世界只剩下我們。我們直視著彼此,堅定不移,身體互相餵養,訴說言語所無法表達之事。我們共舞,我們的舞大膽無畏、毫無保留,比撫摸更親密。我從沒見過凱特如此無拘無束的樣子。我感覺宇宙撕開了一道縫,而我也是。我已無可救藥。
一週後,我們坐在銀湖水庫東北側的草坪上,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,在一本Moleskine小筆記本上塗塗寫寫。我們認為一起拍片是個棒透了的點子,最好是拍愛情片。我和凱特各自發信給我們的演藝代理,希望他們能幫我們找到合作的機會。
事情就這樣動了起來。我們很快就收到一份喬‧巴頓(Joe Barton)所寫的劇本。劇本很短,只有八十幾頁,故事尚待加工與擴展,但一部椎心又唯美的電影骨架已經有了。我們和喬用 Skype 交流想法,他是位可愛的英國人,他筆下的酷兒女性角色刻畫得細緻入微,令我嘆為觀止。我們討論了故事、角色以及我們覺得需要深入發展的地方。
「那部劇本是我很久以前寫的。給我一個月,我會生出一份新版。」喬說。
他說到做到。劇本品質抵達了全新的高度,拍攝計畫也動了起來。
和凱特分開的時光開始讓我感到痛苦。此刻,我們的火花仍在,依舊春心蕩漾,宛若置身雲端,但總有結束的時候。有些地方我們去不了。有些事我本不應該奢望。朋友建議我退一步,而這個提議再合理也不過,畢竟也不是第一次了,有些人你就是得不到。即便我已正式出櫃,險路依舊重重。
「你讓我想到那些老是和已婚男交往的朋友。」一位朋友對我說。總是在追求刺激,然後墜落,執迷不悟。
不久後,講這句話的朋友親眼見到我們在一起的樣子,便恍然大悟了。這個反應讓我感到既欣慰又惱火。我們的愛是有形的,我們在一起的樣子閃閃發光。
可是,還有麥斯。麥斯!麥斯。他是個讓人打從心底喜歡的好人,他一直以來都對我好得沒話說。凱特愛他,怎麼可能不愛?不過,無論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,都是在找尋新的語言,從縫隙中滲出來。算是我默許的吧,而我不該這麼做。我才是那個介入他人認真感情的人。
有一次,我和凱特本來預計要在紐約共度一段時光,孰料計畫突然生變,麥斯決定跟她同行,那是我頭一次嚴重遭受打擊。我期待這段浪漫紐約時光好久了。我很傷心。傷透了心。但,又一次,我把這看成是我自己的問題,身為小三的問題。
我去紐約的目的是為《X 戰警:未來昔日》跑宣傳。在那部片中,我幾乎從頭到尾都坐在休‧傑克曼(Hugh Jackman)身後,他飾演一隻不省人事的金剛狼,我將手放在他的頭兩側,按摩他的太陽穴。休‧傑克曼人超級好,好到有點討厭,是我合作過的人當中最和藹可親的人,我真心沒見過他心情不好的時候。
然而,當凱特告知我這個消息後,我的心情瞬間烏雲密布。看見他們被狗仔拍到在街頭散步令我感覺更糟。想到他們會做愛時,就更不用說了。我在接受喬許‧哈洛維茲(Josh Horowitz)採訪時,有一位名叫凱特的粉絲提問,問我對香蕉的看法。這是我和她私底下會用的哏。凱特是喬許的朋友,她覺得這樣做會很有趣。我花了一秒才把兩者串在一起。這對我來說一點都不有趣。我想她想得很痛苦。
我很生氣。火大。感覺被耍。我很熟悉這種心情模式,這種糾纏不清並為此自責的狀態。我發現自己開始怪罪她:不能和我在一起的時候,她就會想方設法用另一種方式侵踏我的領域,滲透我的心智。我老是會被吸回去,說服自己這樣是健康的,說服我的主體性並未被渴望給緩慢侵蝕。我感覺自己沒有被認真對待,我的感覺被忽視。我很偏頗地假定她應該要能讀懂我的心。我嘴巴上說「當然沒問題」,心裡卻要求她解讀出相反的意涵。
走到這個地步,我其實該退出了。原因有很多,主要是想當個好人,尊重他們的感情,但我感覺自己並不是非常好的人,而是個自私的人,渴望著某人。可是,真切的情感很罕見,就像我們之間的這種,格外稀有,也因此很難割捨。我坐在柏威里飯店的房間,在陽台上抽著菸;我和凱特曾經來過這個房間。我克制不住腦海中閃現她把赤裸的我抱到桌上的畫面,她一邊上我,一邊盯著鏡子裡我的屁股看。
跟凱特有關的一切都變得越來越複雜、越來越沉重。我感到很失望。也許興奮感已經敵不過眼前的挑戰。是我自己選擇要淌這攤渾水的,是我決定不去照顧自己的心,而是選擇留下,無視分歧逐漸加深。我在追求某樣無法實現的事物,任由慾望淹沒自己。
這種心境變化相當熟悉。獨處時你茁壯,隱密又安全,分離卻讓你感覺自己隱形了。上一秒還在,下一秒便消失,連轉念都不是,就成了後話。我把這些投射到了她身上,這是一套我需要時間才能擺脫的模式及敘事——請愛我。
凱特察覺到我的痛苦、我的揪心,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傷害我。她人在外地工作,但還是抽出時間和我聊聊。我告訴她我在紐約所遭受的痛苦。
「我太想妳了,一想到能見妳我就興奮到不行,後來卻落空。我們連一面都見不上,也幾乎沒有妳的消息,然後妳又那樣,」我在說那場訪談。「讓我感覺糟透了。」
「我理解,我真的很抱歉,我只是以為那樣會很好玩。」她停頓了一下。螢幕畫面靜止了片刻。「我也很想你,見不到你我也很難受。」
防洪閘門被這句話打開。我哭了起來,接著她也開始一起哭,我們談起一切。談起我們對彼此的愛,談起這份愛是多麼的渾然天成、感覺多有意義,談起我們對彼此的關心有多深沉。

(圖,合成照/@elliotpage IG、@katemara IG)
「但我也很愛麥斯,而且我們有共同的生活。」她說。「我以前不相信人能夠同時愛上兩個人。但我現在相信了。」
我們同時陷入感傷,嘗到放手的惆悵,但凌駕一切之上的是,我們在乎我們的未來,無論那會是什麼形狀,我們所在意的,是建立一種新的關係。我們同意暫時保持距離,至少一個月不要聯繫。
我需要一再提醒自己保持距離的好處。這麼做令人痛苦難耐,就算是自己主動提議的也一樣。欺騙自己是十分容易的一件事。我會用溝通是很好、很健康、又成熟的行為來說服自己。然而,無論我的大腦理解了多少,那些感受還是會偽裝並埋伏起來,低語撩撥著我的心,讓癮頭再次犯起。
「你讓我想到那些老是和已婚男交往的朋友。」現在的我更能理解這句話了。
的確,我渴望讓血清素飆升,接著耽溺在被拒絕的痛苦之中。最終,我在過程中拋棄了自己,淡出,而或許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;未境的愛更安全,總渴望那些得不到的。
凱特和麥斯在不久後分手,就在我將與麥斯一起拍攝的不久前。他們分手不是因為凱特想和我在一起,而是雙方同意是時候該向前走的結果。我和凱特繼續維持距離。麥斯對我好得沒話說,在片中也表現出色,是個寬厚又投入的演員,合作相當愉快。我們有一場性愛戲,是我拍過最私密的性愛戲之一,我們兩個幾乎是全裸上陣,我的胸部完全坦露在外。那場戲感覺安全又自在,一點違和感都沒有,雖然坦白說是有點怪。
我對凱特還是有感覺,想要她,想要跟她在一起。保持距離很有效。我覺得自己多少已經放下了,但我們發現彼此剛好都回到了洛杉磯,再度回到動心的那座城市。我心情很亂、很氣餒,甚至有點憤恨。她現在可以和我在一起了。但她現在不想和我在一起了。
「單憑愛情構不成一段關係。」我的諮商師常這麼說。
我再次陷入痛苦中。憤怒悄然滋長。
時間緩慢爬行,緩慢癒合。不講話也不傳訊息很有幫助。我慢慢開始釋放、反思、當責。我不再執著,開始能正常約會,去見那些單身且對性向落落大方的女人。朋友湊合我和莎曼珊在一起,我們交往了近兩年。在我和凱特一起製作並出演《決愛》(My Days of Mercy)的期間,莎曼珊曾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郊區找我。她沒有嫉妒,反而很支持我,我們三個還一起去到肯塔基州邊境附近看了一場艾米‧舒默(Amy Schumer)的演出。凱特當時在和傑米交往,也就是她現在的丈夫。
念及當時的情況,拍攝算是進行得非常順利。
我和凱特相識至今將屆九年。某些默契從未消失,但現實的沉澱讓我們笑稱彼此怎麼會差這麼多。事後回想起來,當時我們幾乎都在做愛。不過,我們之間的愛從未變過,往後也不會改變。忠心、寬厚、有情有義——凱特不只是位很棒的朋友,也是最真誠的朋友。
我總是習慣幻想,而非關注或回應實際發生的事。我不聽。說穿了,過去的我就是個容易依賴他人的人。直到現在,我才終於擺脫了那種狀態。我設置了更有效的界線、更少害怕、心態也更加開放。我變得堅強,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,並且急速上升中。啟示和教訓會在我們最黑暗的時刻浮現,雖然,我確定有一天我會忘記這些教訓,不得不再一次想起。但我寧願再次想起,我寧願受傷也不要沒傷過——至少我有機會愛過妳,至少我感覺過妳對我的愛。瑪姬‧尼爾森說:光是見過這種藍,就讓我的生命變得非凡。見過如此美麗的事物。發現自己置身其中。無從選擇。
(延伸閱讀:《艾略特·佩吉自爆和《鴻孕當頭》同劇演員一直做愛:「這是頭幾次有人能讓我高潮!」》)
Source:采實文化、@elliotpage IG、@katemara I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