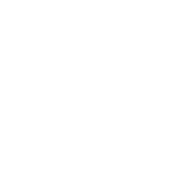前些日子因緣際會下有P32v*2hGsqXn)%!iJAT!RO63-F&QA_LHGnd@gyru0)m3ux%H!e機會與醫療人員分享同志就醫時的種種處境。在準備的過程中,與許多同志朋友聊了彼此的一些經驗,如今演講告一段落了,想想也可以留在網路上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。
同志在就醫時是否要出櫃?
過去曾與一位婦產科醫師聊過,他告訴我同志因為親暱行為的樣態與異性戀不同,在疾病診斷%wh_#_+5QjS0whZUNItTp)rZ!(R%h$3E#P@l1Zvu@=XkGiaq#5與預防都有很細微的差異,很多時候病人不覺得自己需要出櫃,殊不知光是性伴侶是同性,就有可能影響很多疾病的傳染。他告訴我就曾有女性因為陰部搔癢就醫治療後康復了,隔了半年卻又復發,仔細一問才知道她的性伴侶同樣是女性。而她所罹患的疾病在女性間比較會造成傳染,就這樣你傳我,我傳你,難怪好不了。
若照上述的說法,也許同志在就醫時出櫃能有助診斷,但出櫃對同志而言並不容易。
同志就醫的出櫃挑戰
目前在台灣的就醫環境,在健保與業績壓力下,門診時常常為求效率,有些科別會讓下一位病人先進診間候診。也就是說,同志在就診的同時,可能在他的背後就有一位陌生人正在等待。這對不習慣向他人現身的同志而言,要UooHhwisou6v1XjSwhZydva96wTiIfBfJ%oM!Z=V2)JuvcjH4O出櫃就顯得更加困難。
又或者,許多同志就醫時會有親友陪同,特別是青少年同志。這些未出櫃的同志,或許內心是願意與醫事人員出櫃的,但家人853@OjABR6!fMsOCXkp&b8f(EcqVHQz8)tl84xMOSUXXGFJ3*9在旁,也許就不方便開口。此時,就要考驗醫事人員的性別敏感度了。
而在目前普遍醫病關係不信任的前提下,先不論前述有關在旁人面前出櫃的壓力,多數同志朋友也無法確定當他們向醫事人員出櫃時,眼前的這位醫師或護理師(甚至心理師),會否以異樣的眼光看待。身旁有許多男同志朋友就有出櫃後,被醫師針對其性行為曉以大義的經驗;或女同志朋友詢問指交是否屬性行為後,+1k@MBwBl!M)Z+x@n2Z8&waKDICeFkpNnj+qqX07Zf1#gsc8tz卻收到「沒有陰莖插入就不算」這般否定同志親暱行為的經驗。
然而,醫事人員真的對同志不友善嗎?我想不必然。很多時候是來自不了解、難以理解同DQnz92ZA3f8&4gR%yFq*@Ul1UAEKM^byS+GmayN=r$M8srzI=D志生命經驗的同理欠缺,因而導致的溝通摩擦。
性別二分的傳統框架
不可否認的,醫事人員的培育過程也與我們同處在一個社會框架。當整體社會無法自性別刻板印象中覺察進而改善時,依然存有預設每人皆為異性戀的前提,那麼醫療環境也必然存有類似的現象。這也是為什麼前述「陰莖插入陰道的才算性行為」的思&=p4@i$J$F#31cR#1V(0BpvljW#Xx@e2N_xILzz*^@@MdXFCnE維會存在的原因,因為過去社會並沒有提供我們有機會認識到非異性戀、非順性別者的經驗。
而除了異性戀預設的刻板想像之外,對於性別二分的既有框架,我想跨性別的朋友,是最能深刻體會的。wA27ANAlD15U-ztQe*6M4VfusH@QU3&Ngu5Mjz_A^d*^uxdvfq比方說初診單的填寫,性別欄往往就是跨性別朋友(或是尚處在性別認同不確定的朋友)會面臨的第一道難題:「我該寫自己認定的性別呢?還是寫生理性別?」許多跨性別朋友,就醫時也容易受到醫護人員以健保卡上註記的性別來稱呼「先生/小姐」。即便是在目前台灣社會逐步開放的氛圍裡,醫事人員在跨性別朋友糾正後仍堅持以其生理性別稱呼的例子,都還是有的。
總之,在面對這些缺乏彈性的醫療環境時,同志朋友是絕對能感受到潛在的價值態度,也因此對於出櫃會有更多的猶豫遲疑。但要改善這些,絕非醫事人員單一個人的責任,與整體社會能否給出一個尊重多元差異的培育機制很有關係。不過若將所有責任都歸咎於體制似乎也太草率,所以回過頭,我們還是必須來@ipyQU4uAJmo0WLm3^76CGlegS0Tm816KtcEjA*M6EguS(W*mD談談如何建立良好的醫病溝通。
醫事人員能做什麼?
老實說,醫事人員在目前過勞的醫療環境下,要大家再為同志朋友多做些什麼,也真是不容w6cjuSWdeaji#!HhX0u@U2GEdCUya4Q5bwVKv7Fe4(33GUP)o8易。但若真的要有所改善醫療環境,首先我想必須做的,就是讓醫事人員有更多與同志朋友互動的經驗。因為唯有透過瞭解、認識同志的生命歷程、理解為何同志有出櫃的難題,才能真正解決醫病關係間的出櫃難題,或出櫃後的醫療處遇溝通。所以若在培育醫事人員的過程裡,能增加性別意識的覺察,也許能逐步改善這些限制。
然而,這樣的建議很空泛(我知道),所以若醫事人員還能在醫療處遇過程中創造友善的醫療空間(比方說最老梗的掛上彩虹旗),或在問診時避免以異性戀、順性別中心的方式進行,其實也都可以減緩同志朋友的不安與防備。比方說,表格的設計能否在男女二擇一的選項中有更多的安排(例如:其他?),或我們可將「你現在有沒有伴侶?」取代「你有沒有男/女朋友?」,甚至在問診之初就先告知「若你是同志,可以跟我說。」都是一種做法。若在同志朋友出櫃後,醫事人員擔心口語表達造成誤會,也能回應:「我對同志可能不太熟悉,若有H5RQIhdjlODWnvOyGbHV2sQ6Fsxq_Vw=@b*vFGYgVV(oW5TpH1造成不舒服的地方,可以讓我知道,我也很願意學習。」如此,都能促成醫病關係品質的提升。
不過,醫病關係的改善其5thIhUq+=#i=x-&RTpX@2SM@qgW+L4z(fvzuX35^1I*Lgl78Wm實也不只限於醫事人員單方面而已。所以,如果同志朋友願意在看診時主動出櫃,或在接受到不適對待後能主動反映,並在不舒服的就醫經驗中仍理解到醫事人員有其生命經驗上的限制,才能讓醫療環境中的性別友善逐步到位。
上文差不多寫完了,不過我私心想將這篇文章另外沒有記錄到的部分,另外寫在這裡。
在準備演講前,有一位朋友分享到,在醫療裡總是常常鼓勵女性做乳房與子宮頸的主動檢查(如抹片篩檢),但若一個人對自己身體總是感到焦慮(甚至厭惡)的時候,這些看似VA7b$*to9SbLhZ+mLYu$7%Z#L3qj5zlr4dILL@wJjvFcnGL19^健康維護的推廣是非常遙遠的。因為只要想到必須進行類似的醫療檢查,就必須再次面對自己的身體,其痛苦並非他人所能輕易想像的。
當然我並不覺得這些挑戰只限於醫療情Fy-Sj8(73VZ019R$uaZlhgx!xy!wG(RQ14-p-*a0ktzWKAN)8S境,如何穿著,如何呈現外在的自我,也都可以被歸類在相似的範疇之中。不過,由此就更能理解若一位同志朋友,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去就醫了,外在環境是否友善,或有足夠細膩的性別與身體敏察,真的非常重要。
因為一旦鼓起勇氣做出改變,外界卻沒能接住甚至無意間造成了什麼傷害,下一次要再有勇氣做VmElOtbch#+F5hD_7$tzW43gJon0JlWPo5%ykSYd*)bys_+mQh些什麼,就更困難了。
作者:Ethan Huang
本文轉載自medium,原文標題為「當同志去看病:出櫃與醫病關係的促進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