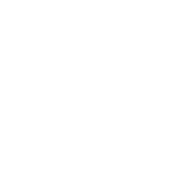這本書,紀念了那個「同志」還是禁忌、還不可大聲言說的時代,其中的混亂、不安、悲傷與努力。
即使她是個女人
但她可以深深進入我的最內裡
達到任何男人都無法觸及的深度
《惡女書》的第一篇〈尋找ArQSxaE%=Wh0G)hpbO&@N*XIzNL=CKz%9Q*KCsiGR+G-NMTJ*P天使遺失的翅膀〉,是我至今被收錄、轉載、研究最多次的作品,那是我在大學快畢業時,坐在地板上就著一個木箱子鋪上稿紙用鋼筆寫下,當時我用父親給的音響,一邊聽顧爾德一邊寫稿,猶如現在一樣。
我不055VVfQhSGnq&Bv3Oi-1#0V69(A*^)UYhfF4DJeo8#PaTXL5(l知道自己的書即將掀起巨浪,掀翻我自己這艘顫危危的破船,而這道浪也把我提早推進了「作家」這個身分裡,這本小小的書充滿連作者自己都沒有察覺的力量,那是年輕、狂熱、無所畏懼也無所求的寫作者才能擁有的力量。--陳雪

女同志作家陳雪。(圖/臉書)
《惡女書》共收錄〈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〉、〈異色之屋〉、〈夜的迷宮〉、〈貓死了之後〉四則短篇小說。
以第一人稱告白體,書寫女同性戀充滿罪惡感卻ZjyjI3UB3=+S%Y7#X1z4g&S@K@$3OPOqM^KEyqpafDKWm4t9Il又耽溺其中的情欲,在看似淫蕩敗德的字裡行間,流露的是被社會主流價值所壓抑的痛苦與悲哀。陳雪述說的是關於「人內在」的故事,不只是女性的,不只是同性戀的,更不只是情欲的,而是企圖用文字與肉身極力抵抗所謂「唯一的真實」。
當我第一眼看見阿蘇的時候,就確定,她和我是同一類的。我們都是遺失的翅膀的天使,眼睛@*J@@RO@jj9zJbB(1cFNy9R)FRDkF@-s*iVHvaQxXdAF%V_^-o仰望著只有飛翔才能到達的高度,赤足走在炙熱堅硬的土地上,卻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方向。--〈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〉
「那屋子的女人們。」這是村人給她們的名字。女人的屋子、女人的糕餅、女人的孩子……=ZSwr)Gix1&UO6bQ^RdTjv_5(rqg0llv$bfTD^Wqb(y^e=nsUa村人既嫌惡又好奇,膽顫心驚地私下議論紛紛。自此,連天氣都走樣了。--〈異色之屋〉
「為什麼我們仍要一次次去走那些無用的迷宮呢?」「因為,我們都是實驗用的白老鼠啊!」--〈夜的迷宮〉
在貓店看見那隻貓,我才知道,我一直在想念她。阿貓化身成各種形象出現在我的生活中,為的是不讓我逃避自r#_BSHFAbY%r1u@oU#72mu$mySx+(bF(r%XYR-MfK$$VtFP&ZM己。--〈貓死了之後〉
《惡女書》新版序 那些我想永遠記住的

《惡女書》。(圖/印刻文學)
《惡女書》是我的第一本小說集,收錄〈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〉、〈異色之屋〉、〈夜的迷宮〉、〈貓死了之後〉四個短篇小說,第一次出版於一九九五年九月,二○○五年新版重出,*Y1vEi82%(kIw__NMf-e+Fz6tB7yUJXzClBGBD$KebS0U19lx-時間來到二○一八年,再次於印刻文學重新出版。
安靜的午後,我在家裡的客廳書桌寫長篇,屋裡明亮寬敞,生活作息全憑我自己安排,我聽著顧爾德彈巴哈,這是寫作的儀式,彷彿顧爾德的手指落下、敲響琴鍵,我就有直覺可以落下手指、敲動鍵盤。《哥德堡變奏曲》第一版CORhIMfEYiedR+H3fsHg7TTSPALl0B_majK(hcFk6OMm&exT)Z出版於一九五五年,一九八一年顧爾德重新演繹了這個曲子,年輕時與中年後的顧爾德分別彈奏錄製了這個曲子,年輕的我偏愛年輕的顧爾德,到了中年的我,聽懂了中年的顧爾德。
《惡女書》的第一篇〈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〉,是我至今被收錄、轉載、研究最多次的作品,那是我在大學快畢業時,坐在地板上就著一個木箱子鋪上稿紙用鋼筆寫下,當時我用父親給的音響,一邊聽顧爾德一邊寫稿,猶如現在一樣,當年我只是個小說練習生,對於小說、同志、性別理論懵懵懂懂,腦中燃燒得更多都是對寫作的狂熱,我沒想過如何成為作家,如何出版書籍,將來以何維生,我只曉得要寫,正如書中角色草草的心境,能寫就能活。我不知道自己的書即將掀起巨浪,掀翻我自己這艘顫危危的破船,而這道浪也把我提早推進了「作家」這個身分裡,這本小小的書充滿連作者自己都沒有察覺的力量,那是年輕、狂熱、無所畏懼也無所求的寫作者才能擁有的力量,多年後我重看這些稿子,看得到自己當年的生澀,天真,也看到了我不可能QTK6#62S^mfTwZ=I@6Pf$Dl&LbRinEc)bHjSiwioAe_03q7qAC再擁有的那股生猛強烈的力量。
《惡女書》一九九五年出版時曾引起過重大的爭議,後來很長的時間裡,我對於這本書總是夾雜著複雜的情緒,我既寶愛自己的第一本書,卻也恐懼旁人看待我時只記得我寫過這本書,或許因為這股矛盾的情緒,促使我一本一本地寫長篇,使我終於走出AZMqXFdpc8MLi)YG%ZOdeL+=YLp62RS!lPAB)*uOt%*t0*x0Lr了自己小說的道路。
我沒有如顧爾德那樣於中年時重新演繹,然而在同志婚姻即將合法,又面臨各種阻礙之際,這本書能夠再次出版,對我意義重大。這本書不但是紀念我所經歷過那個困難的時代(無論是對於同志,或對於我自己),也記錄了我作為小說寫作者艱難的起步,我在每一個短篇裡看到自己在端盤子、洗碗、送貨、擺地攤,我看到自己在各種不適宜寫作的時空裡!BVM9=ZGwMp3L=zD7so!8PpwN3YR%AN^rqY4qd4fa&S)WDg%Hm努力地擠出時間,找出位置,在夜市的攤位上,在黃昏市場對面的小咖啡店,在家裡的陽台,在房間的地板,在各種工作的檯面上,用鋼筆一字一句書寫著,二十多年過去,我終於可以平靜地看待她,如果她是個女兒,也該二十多歲了,我不用再逃避她了。
祝福這本書。祝福所有閱讀她的人。
內容試閱:
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
當我第一眼看見阿蘇的時候,就確定,她和我是同一類的。
我qlA&OHyjij6q-FW4zjXS-a=q-omDn%8D0tYomUc1rvY7Krg$=i們都是遺失了翅膀的天使,眼睛仰望著只有飛翔才能到達的高度,赤足走在炙熱堅硬的土地上,卻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方向。
◆
黑暗的房間裡,街燈從窗玻璃灑進些許光亮,阿蘇赤裸的身體微微發光,她將手臂搭在&U)sNuQyt1_%#O+V6ng4fCQunXo*aWME_@w1o5%yMpj@W(R-MR我肩上,低頭看著我,比我高出一個頭的地方有雙發亮的眼睛,燃燒著兩股跳躍不定的火光⋯⋯
「草草,我對你有著無可救藥的欲望,你的身體裡到底隱藏著什麼樣的祕密?我想知道你,品嘗你,進入你⋯⋯」
阿蘇低沉喑啞的聲音緩緩傳進我的耳朵,我不自禁地暈眩起來⋯⋯她開始一顆顆解開我的釦子,脫掉我的襯衫、胸罩、短裙,然後我的內褲像一面白色旗子,在她的手指尖端輕輕wA%uyI(kxnyaEk=C!)SQ*mrj2L9ZYWhsNV9(lBDm_WD#GocaR%飄揚。
我赤裸著,與她非常接近,這一切,在我初見她的剎那已經注定。
她輕易就將我抱起,我的眼睛正對著她突起的乳頭,真是一對美麗得令人慚愧的乳房,在她面前,我就像尚op=LKp1+i&-Rf*K!IhU4HO3Dkd64)8X_Awao+xu6l@$MvzXVum未發育的小女孩,這樣微不足道的我,有什麼祕密可言?
躺在阿蘇柔軟的大床上,她的雙手在我身上摸索、游移,像唸咒一般喃喃自語。
「這是草草的乳房。
「這是草草的鼻子。」
⋯⋯
從眼睛鼻子嘴巴頸子一路滑下,她的手指像仙女的魔棒,觸摸過的地方都會引發一陣歡愉的顫慄。
「草草的乳房。」
手指停在乳頭上輕輕劃圈,微微的顫慄之後,一股溫潤的潮水襲來,是阿蘇的嘴唇,溫柔的吸吮著。
最後,她拂開我下體叢生的陰毛,一層層剝開我的陰部,一步步,接近我生命的核心。
「有眼淚的味道。」
阿蘇吸吮我的陰部我的眼淚就LwJr=mp-Ybg=Aetag&EQ2=58TA=V$fylmZN3FX^gbq_j5dP!dl掉下來,在眼淚的鹹濕中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,彷彿高燒時的夢魘,在狂熱中昏迷,在昏迷中尖叫,在尖叫中漸漸粉碎。
我似乎感覺到,她正狂妄地進入我的體內,猛3Ndh_A$ZV1g+)$cWC@cfA(pSD+Dnk)^-(gI1G@As9aiSY=BTNk烈的撞擊我的生命,甚至想拆散我的每一根骨頭,是的,正是她,即使她是個女人,沒有會勃起會射精的陰莖,但她可以深深進入我的最內裡,達到任何陰莖都無法觸及的深度。
◆
我總是夢見母親,在我完全逃離她之後。
那是豪華飯店裡的一間大套房,她那頭染成紅褐色的長髮又蓬又捲,描黑了眼線的眼睛野野亮亮的,幾個和她一樣冶豔的女人&ONm7SGmQ6#^k)SWgD0KQ(%A79ASSB#*yLHU77VchEL0TL(=WT,化著濃妝,只穿胸罩內褲在房裡走來走去、吃東西、抽菸,扯著尖嗓子聊天。
我坐在柔軟的大圓床上,抱著枕頭,死命地啃指甲C0oTXV4B@kfvyUPgX@I=hr(DWWBPZg2*e$B8IRpIBG7#5a-)XS,眼睛只敢看著自己腳上的白短襪。一年多不見的母親,這究竟是怎麼回事?她原本是一頭濃密的黑色長髮,和一雙細長的單眼皮眼睛啊!鼻子還是那麼高挺,右眼旁米粒大的黑痣我還認得,但是,這個女人看來是如此陌生,她身上濃重的香水味和紅褐色的頭髮弄得我好想哭!
「草草乖,媽媽有事要忙,你自己到樓下餐廳吃牛排、看電影,玩一玩再上來找媽媽好不好?」
她揉揉我頭髮幫我把辮子重新紮好,塞了五百塊給我。
我茫然地走出來,在電梯門口撞到一個男人。
「妹妹好可愛啊!走路要小心。」
那是個很高大、穿著西裝的男人。我看見他打開母親的房門,碰一聲關上門,門內,響起她的笑聲。
我沒有去吃牛排看電影,坐在8jItr#UTH^bsryGb!6AS60h6P&2AH=WPpog+QsjTN^-sCEhBgH回家的火車上只是不停地掉眼淚,我緊緊握著手裡的鈔票,耳朵裡充滿了她的笑聲,我看著窗外往後飛逝的景物⋯⋯就知道,我的童年已經結束了。
那年,我十二歲。
完全逃離她之後,我總是夢見她。一次又一次,在夢中,火車總是到不了站,我的眼淚從車窗向外飛濺,像一聲嘆息,天上的雲火紅滾燙,是0QDYWMYg1n8dBtqBIAsx4isWM&ZrIjP3Gy-aiRTzy5IR*S0aMi她的紅頭髮。
◆
「你的雙腿之間有一個神祕的谷地,極度敏感,容易顫慄,善於汩汩地湧出泉水,那兒,有我極欲探索的祕密。
「親愛的草草,我想讓你快樂,我想知道女人是如何從這裡得到快樂的?」
阿蘇把手伸進我的內褲裡搓揉著,手持著菸,瞇著眼睛朝著正在寫稿的我微笑。
我的筆幾乎握不穩了。
從前,我一直認為母親是個邪惡又淫穢的女人,我恨她,恨她讓我在失去父親之後,竟又失去了對母親的敬愛,恨她在我最徬徨無依c&VtU=P$3fMmHMn1QA$(2Ii^%T9mMt-7_faa(e@iW)S%Jqu8kg時翻臉變成一個陌生人。
恨她即使在我如此恨她時依然溫柔待我,一如往昔。
遇見阿蘇之後我才知道什麼叫做淫穢與邪惡,那竟是我想望已久的東西,而我母親從來都不是。
阿蘇就是我內心欲望的化身,是我的夢想,她所代表的世界是我生命91$N)EaX2W9FEqAa&87VRI7%&#KwqX!-!!6(uhsTl0jx)vl!hS中快樂和痛苦的根源,那是育孕我的子宮,脫離臍帶之後我曾唾棄它、詛咒它,然而死亡之後它卻是安葬我的墳墓。
◆
「我寫作,因為我想要愛。」
我一直感覺到自己體內隱藏著一個閉了的自我,是什麼力量使它 閉的?我不知道;它究竟是何種面目?我不知道;0o%oa&lAN*bX9Uv7mWp4Y!XYJyv-BxP6_aeZ4IM(Kb(Zp4lIhg我所隱約察覺的是在重重封鎖下,它不安的騷動,以及在我扭曲變形的夢境裡,在我脆弱時的囈語中,在深夜裡不可抑制的痛苦下,呈現的那個孤寂而渴愛的自己。
我想要愛,但我知道在我找回自己之前我只是個愛無能的人。
於是我寫作,企圖透過寫作來挖掘潛藏的自我。我寫作,像手淫般寫作,像發狂般寫作,在寫完w836ovqy5mfhl!pmlmAg4Dq^W*T5mvlNC#v8V7_$&HwTuPN^Rw之後猶如射精般將它們一一撕毀,在毀滅中得到 交時不可能的高潮。
第一篇沒有被20b^eT*QZ-K+*cK+)7PpF$NztzUYGjw!Hw71MPt)aMs)AT6YfV我撕毀的小說是〈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〉,阿蘇比我快一步搶下它,那時只寫了一半,我覺得無以為繼,她卻連夜將它讀完,讀完後狂烈地與我做愛。
「草草,寫完它,並且給它一個活命的機會。」
阿蘇將筆放進我的手裡,把赤裸著的我抱起,輕輕放在桌前的椅子上。
「不要害怕自己的天才,因為這是你的命運。」
我看見戴著魔鬼面具的天才,危危顫顫地自污穢的泥L^u#FXeIIZm#kbZTzOjkXtHK1o-3$-+0NiLORh_8zN_lG#T=Ix濘中爬起,努力伸長枯槁的雙臂,歪斜地朝向一格格文字的長梯,向前,又向前⋯⋯
◆
曾經,我翻覆在無數個男人的懷抱中。
十七歲那年,我從一個大我十歲的男人身上懂得了性交,我毫不猶豫就讓他插入雙腿之間,雖然產生了難以形容的痛^%53*)9GqswA+ITjf!VuK-oxX1%hcHN7CXV&w7Hwp^*ycFF=0t楚,但是,當我看見床單上的一片殷紅,剎那間心中萌生了強烈的快感,一種報復的痛快,對於母親所給予我種種矛盾的痛苦,我終於可以不再哭泣。
不是處女之後,我被釋放了,我翻覆在無數個男人的懷抱中以為可以就此找到報復她的方法⋯⋯
我身穿所有年輕女孩渴望的綠色高中制服,蓄著齊耳短髮,繼承自&8(%ldbR@dlmExFUkT88gbr#Qb3u$2vqf8M+(OKSyjhB%RkHct母親的美貌,雖不似她那樣高,我單薄瘦小的身材卻顯得更加動人。
旁人眼中的我是如此清新美好,喜愛我的男人總說我像個晶瑩剔透的天使,輕易的就攫獲了他們的心。
天使?天知道我是如何痛恨自己這個虛假不實的外貌,和所有酷似她的特徵。
我的同學們是那樣年輕單純,而我在十二歲那年就已經老了。
「天啊!你怎麼能夠這樣無動於衷?」
那個教會我性交的男人在射精後這樣說。
他再一次粗魯的插入我,狠狠咬VqAz%&oUhM=!pM_z_XIaApK$h8l)^Ps@nLUQZSo-5DB=sWB#Ac嚙我小小的乳頭,發狂似的撞擊我,搖晃我。他大聲叫罵我或者哀求我,最後伏在我胸口哭泣起來,猶如一個手足無措的孩子。
「魔鬼啊!我竟會這樣愛你!」
他親吻著我紅腫不堪的陰部,發誓他再也不會折磨我傷害我。
我知道其實是我在傷害他折磨他,後來他成了一&4H+ipeRDK7+*-IT8JhceXIr@D@WqHO6soSYXRY9gF98u6(jGw個無能者,他說我的陰道裡有一把剪刀,剪斷了他的陰莖,埋葬了他的愛情。
剪刀?是的,我的陰道裡有一把剪刀,心裡也有!它剪斷了我與世上其他人的聯繫,任何人接近我,都d1UIT&AA3+rvFRZl^OT!^PeB19ERo^fEy7E^Adh=YHRZW)RPY2會鮮血淋漓。
◆
記不得第一次到dd9WJuxAD1=otnih=JKeZH)bR&!7M!KaoHw1u)ELUjS4kNdcoO那家酒吧是什麼時候的事了?總之,是在某個窮極無聊的夜晚,不分青紅皂白闖進一家酒吧,意外地發現他調的「血腥瑪麗」非常好喝,店裡老是播放年代久遠的爵士樂,客人總是零零星星的,而且誰也不理誰,自顧自的喝酒抽菸,沒有人會走過來問你:「小姐要不要跳支舞⋯⋯」當然也是因為這兒根本沒有舞池。
就這樣,白天我抱著書本出入-0Bs60_&UehAPf#Jp(vEw00VnNnLO^u&wcU9!Vb6HVS6nsme#3在文學院,像個尋常的大學三年級女生,晚上則浸泡在酒吧裡,喝著他調的血腥瑪麗、抽菸、不停地寫著注定會被我撕毀的小說。他的名字叫FK,吧檯的調酒師,長了一張看不出年紀的白淨長臉,手的形狀非常漂亮,愛撫人的時候像彈鋼琴一樣細膩靈活⋯⋯
後來我偶爾會跟他回到那個像貓窩一樣乾淨的小公寓,喝著不用付錢的酒,聽他彈著會讓人骨頭都酥軟掉的鋼琴,然後躺在會吱吱亂叫的彈簧床QARS6_qVR3V&kOC1VwvbB085SgXpZ7i#AMrX2)WR^yZ6FRpCzj上懶洋洋地和他做愛。他那雙好看的手在我身上彈不出音樂,但他仍然調好喝的血腥瑪麗給我喝,仍然像鐘點保母一樣,照顧我每個失眠發狂的夜晚。
「草草,你不是沒有熱情,你只是沒有愛我而已。」
FK是少數沒有因此憤怒或失望的男人。
看見阿蘇那晚,我喝了六杯血腥瑪麗。
她一推開進來,整個酒吧的空氣便四下竄動起來,連FK搖調酒器的節奏都亂了⋯⋯我抬頭看她,只看見她背&OO$fwT#jp!55+vthZ72-5*#H01xzL-Dy4vp)7W4rgXilmW1g^對著我,正在吧檯和FK說話,突然回頭,目光朝我迎面撞來,紅褐色長髮抖動成一大片紅色浪花⋯⋯
我身上就泛起一粒粒紅褐色的疙瘩。
我一杯又一杯的喝著血腥瑪麗,在血紅色酒液中看見她向我招手;我感覺她那雙描黑了眼線亮亮野野的眼睛正似笑非笑地瞅著我,我感覺她那低胸緊身黑色禮服裡包裹的身體幾乎要爆裂出來,我感覺她那低沉喑啞的聲音正在我耳畔呢喃著淫keUhJrW95@wUCHKKBA%F#Cc_qApn&Olb5$gm&UzmuZWMIca&X9穢色情的話語⋯⋯恍惚中,我發現自己的內褲都濡濕了。點燃我熾烈情欲的,竟是一個女人。
她是如此酷似我記憶中不可觸碰的部分,在她目光的凝視下,我彷彿回@p=$iCyHLtBVgp!H*Fr%kQFietVXwaW9X!gU7kUZ!(%Gx(a8R+到了子宮,那樣潮濕、溫暖,並且聽見血脈僨張的聲音。
我一頭撞進酒杯裡,企圖親吻她的嘴唇。
在暈眩昏迷中,我聞到血腥瑪麗自胃部反嘔到嘴裡的氣味,看見她一步一步朝我走近⋯⋯一股腥羶的體味襲來,有個高大豐滿多肉w=&Tp9y^m3gvJrdG_Oq#vK89aPT5dvvE*wf%KZux9faE((qfjQ的身體包裹著我、淹沒了我⋯⋯
◆
睜開眼睛首先聞到的就是一股腥羶的體味,這是我所聞過最色情的味道。
頭痛欲裂。我努力睜開酸澀不堪的眼睛,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大得離譜的圓床上,陽光自落地窗灑進屋裡,明亮溫暖。我勉強坐起身,xqT1E!G=uLUHLtj5D^Y6+kAUiMLUc+1dqmQNMFn)W)Gn!y)9CH四下巡視,這是間十多坪的大房間,紅黑白三色交錯的家具擺飾,簡單而醒目,只有我一個人置身其中,像一個色彩奇詭瑰麗的夢。
我清楚的知道這是她的住處,一定是!我身上的衣服還是昨晚XAcvTqICsL9fmh!#Ta9hOQtAn51D5rkBNqYpM7&^3Cahf6KW$=的穿著,但,除了頭痛,我不記得自己如何來到這裡?
突然,漆成紅色的房門打開了,我終於看見她向我走來,臉上脂粉未施,穿著T恤牛仔褲,比我想像中更加美麗。
「我叫阿蘇。」
「我叫草草。」
來了!
◆
當我第一次聞到精液的味道我就知道,這一生,我將永遠無法從男人身上得到快感。
剛搬去和母親同住時,經常,我看見陌生男人走進她房裡,又走出來。一次,男人走後,我推開她的房間,看見床上零亂的被褥,聽見$DF=UAee1lRVyFMXo6Hrj9U4If_hq@O(*G^p)%+5Q*@1)hKGFl浴室傳來嘩嘩的水聲,是她在洗澡,我走近床邊那個塞滿衛生紙的垃圾桶,一陣腥羶的氣味傳來⋯⋯那是精液混合了體液的味道,我知道!
我跑回房間,狂吐不止。
為什麼我仍要推開她的房門?我不懂自己想證明什麼%1ICc328k(2PVcQ2qH!NzDag6vbjH%LzoMP(pF7Azj&I@LD)#B早已知道的事?我彷彿只是刻意的、拚命的要記住,記住母親與男人之間的曖昧,以便在生命中與它長期對抗。
那時我十三歲,月經剛來,卻已懂bH%7svFHcdTBcZZ@brvG8u$F2SUl4z)2z%ag^i=3e8!tH)Wudb得太多年輕女孩不該懂的,除了國中健教課上的性知識以外,屬於罪惡和仇恨的事。
對於過去的一切,我總是無QwdgOaB^)_@wUq#$60+==4-rvpEM6C^Xp)p&Kk&$4QI3ylqSGX法編年記述,我的回憶零碎而片段,事實在幻想與夢境中扭曲變形,在羞恥和恨意中模糊空白,即使我努力追溯,仍拼湊不出完整的情節⋯⋯
所有混亂的源頭是在+rPgltNMpVCfw-_LV4(GWw7-bH2ZycaPjhG*6Z2eqC2EFL+H-v十歲那年,我記得。十歲,就像一道斬釘截鐵的界線,線的右端,我是個平凡家庭中平凡的孩子,線的左端,我讓自己成了恐懼和仇恨的奴隸。
那年,年輕的iEFLm$)5hBF$rM%q(v2vryb8Df5WTO1Ofg$1QN6Z-_QrCvt5O$父親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出了車禍,司機逃之夭夭而父親倒在血泊中昏迷不知多久。母親東奔西走不惜一切發誓要醫好他,半個月過去,他仍在母親及爺爺的痛哭聲中撒手而逝。
一個月後,母親便失蹤了。
我住在鄉下的爺爺家,變成一個無法說話的孩子,面對老邁的爺爺,面對他臉上縱橫的涕淚,n2D_UwX@PBsE#EL=lH15uUxl8t2aa*Drz1MEY!p!zyrDsEO*pb我無法言語,也不會哭泣。
我好害怕,害6XFUmy^5lG@S3Dg6@MviI39Apof6T3dR+O@G$&to+@+Ghk7$ai怕一開口這個惡夢就會成真,我情願忍受各種痛苦只求睜開眼睛便發現一切不過是場可怕的夢,天一亮,所有悲痛都會隨著黑夜消逝。
我沒有說話,日復一日天明,而一切還是真的,早上醒來陽光依舊耀眼,但我面mLKc&L#_H2x*LIYnL_GIJ(3&Wmj8VaFPWkr!fIVNQLRL4ct-4D前只有逐漸衰老的爺爺,黑白遺照上的父親,和在村人口中謠傳紛紜、下落不明的母親。
「阿蘇,為什麼我無法單純的只是愛她或恨她?為什麼我不給她活下去的機會?」
我吸吮著阿蘇的乳房,想念著自己曾經擁有的嬰兒時期,想念著我那從不曾年老的母親身上同樣美麗的乳房,想著我一落地就夭折的愛情⋯⋯不自覺痛哭起來2CpBnCb1$eOmq3B4#4_Fw_wfu6n6YL$Sx0ck=$AXnehQ&)iU7+⋯⋯。
作者簡介 陳雪
台灣台中人,199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《惡女書》,著有短篇小說集《惡女書》《蝴蝶》、長篇小說《惡魔的女兒》、《橋上的孩子》、《陳春天》、《無人知曉的我》、《附魔者》、《迷宮中的戀人》、《@4vUq67Q#YsU@GdmbNl4=FHT#h42&r)s)^f%+oxhSkrPIvp+Nu摩天大樓》。
source:印刻文學